新冠疫情开始和结束/新冠疫情开始和结束时间
2020年初的那个寒冬,一种未知的病毒悄然划开了时间的表皮,我们为那个时刻贴上了标签:“新冠疫情开始”,它像一个突兀的裂口,将生活粗暴地分为“之前”与“之后”,我们戴上口罩,退入方寸屏幕,用“封控”、“流调”、“健康码”这些新生的词汇,试图编织一张围堵病毒的网,那个“开始”,是如此的清晰、尖锐,带着全球每日攀升数字的沉重与恐慌。
我们曾如此渴望一个同样清晰的“结束”,想象它会像一场暴雨骤歇,会有钟声鸣响,会有宣告胜利的旗帜飘扬,我们等待着“清零”,等待着“摘口罩的那一天”,仿佛只要一个权威的宣言,生活就能像倒放的录像,一切复归原位,那个想象中的“结束”,是一个句点,是隧道的出口,是我们可以集体跨过的门槛。

时间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、甚至有些模糊的答案,病毒的变异,像狡黠的对手,不断改写游戏的规则,防疫的策略,从“围堵”悄然转向“共处”,我们并没有迎来一个万众欢腾的“胜利日”,而是步入了一个漫长的“过渡期”,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终结,新闻的热度逐渐降温,但病毒并未消失,它成为了季节性的背景音,那个期盼中斩钉截铁的“结束”,被拉长、稀释,变成了一种缓慢的“淡出”。

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时间的褶皱里。“开始”的创伤记忆尚未褪色——“结束”的形态却已无从指认,我们部分地取回了2019年的生活,却又永远地失去了某些东西,远程工作成为常态的一部分,对人群密集的微妙警惕深植内心,全球化的天真信念留下了永久的划痕,疫情没有“结束”,它只是沉降了,从一场海啸化为我们精神地貌中一片内化的海洋,持续影响着气候。
这模糊的尾声,或许正是历史本来的质地,重大事件很少有干净的起止,它们的“开始”往往在更早的伏笔中就已埋下,它们的“结束”则化为漫长的遗产,渗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,新冠疫情教会我们的,或许正是放下对清晰边界线的执念,重要的不再是寻找那个神话般的“结束”之日,而是理解我们如何被这段褶皱的时间所塑造,并带着这份复杂的烙印,去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“之后”。
开始与结束,从来不是时间的两个端点,而是我们理解自身叙事的方式,当疫情的惊涛化为历史的余波,我们终于明白,生活不是在“结束后”重新开始,而是带着所有的“经过”,持续地展开。


![[推荐]“樱花互粉真的有挂吗”(原来确实是有挂) [推荐]“樱花互粉真的有挂吗”(原来确实是有挂)](https://ts.weiyanzm.cn/zb_users/cache/thumbs/9ea5eadd90ea3b7af0e6985f6974bd81-300-200-1.jpg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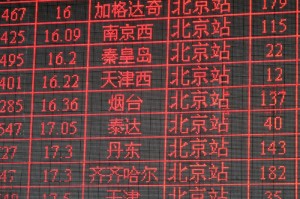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